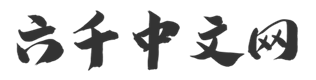楔子回望1笑间弹指五十年
灰暗的灯光下,已达知天命的王大新黯然环视了不足二十平的地方,早已没有了当年意气风发,指点江山的气概。
作为一代书圣王羲之六十八代孙王大新,自视书法造诣颇高,奈何在当今社会新人辈出的年代,毛笔写秃了几支,耗花了不少钱财,也仅仅混了一本市级书法家协会会员证书。
现实社会竞争激烈,创业也失败了,亏得一塌糊涂。
“怎么越混越差了呢?”
王大新喃喃自语,抓了抓日渐稀少的头发。
回首往事,王大新似乎有苦说不得。
王大新出生在物质资源贫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从小被灌输正统思想,王大新骨子里还是想做点不一样的事业的。
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,因为王大新父亲会手艺,有修修补补的活干,可以多拿些工分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倒还不至于断粮。
王大新从小喜欢鼓捣鼓捣,家里有个闹钟,里面有只小鸡在啄米,他拆开了,摸不着头脑的干了半天,等组装起来的时候,失了一个小零件,这小鸡再也无法啄米了。
农村经常断电,一到晚上就煤油灯,或者蜡烛,全村一片黑。王大新家有个蓄电池能用小灯泡白晃晃的亮一晚上,比煤油灯光亮不知有几倍了,也被王大新鼓捣坏了。
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,不知是吃喝不卫生还是那时的条件太差,王大新小时候经常浑身有脓包,还伴有发热。去医院看病虽不贵,得步行**里路才有卫生院。头上的,身上的脓包,都是王大新母亲拿火烤过的剪刀捅破挤掉脓水解决的。
那时农村不注意卫生,小孩肚子里大多都有蛔虫,杀蛔虫的叫宝塔糖,粉红色甜咪咪的,供销社村店有卖,吃上几颗就能杀死它,随着大便排出体外。王大新想起来有点恶心,当时还用手拉蛔虫,不仅仅是下面拉,居然有一次是从口里钻出来,这是其他小伙伴没有经历过的怪事,有点不可思议,至今困惑不解。
还有一年,灰暗的灯光下母亲给他掏耳屎,不知怎么的有只飞蛾飞进了王大新的左耳,扑棱扑棱的,怎么掏也赶不出来了,嗡嗡作响的在耳朵里折腾了几天几夜,最终可能饿死在里面了。
上学后的王大新学习成绩倒也不错,小学一年级还当了小老师课代表。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脑子好像开始出现神游状态了,课堂上居然把女老师叫成妈妈了,神神叨叨的,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这样的状态,幸亏不是经常的,直到初三的时候,才又出了一次。
那是在上数学课,王大新看着女老师在粉笔上写着写着,眼前渐渐白茫茫一片,耳边漂来的声音渐渐的远去,慢慢的悄无声息了。
王大新不敢动弹,在白茫茫的世界里,什么都看不到,没有声音,没有图像,好一阵才恢复正常。
好心的同桌居然在王大新的头上找到了一根白发,才十三四岁的孩子,居然有了白发。
王大新呐呐自语道:
“看来得加强武术锻炼了,要不然肯定得未老先衰”。
刚好那年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电影大行其道,风靡一时,学校图书室,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武侠小说。
王大新总是在放学后跑着过去排队挑到一些自己想看的书,原因是窗口里面借还书那眉清目秀、轻盈苗条的小梅助理,是同班同学。
王大新不自觉地卷入了那场狂热的学武大潮中,和同学开始起早摸黑的在学校小树林里操练着,倒也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好些套路。
太极剑,太极拳,十八罗汉拳,金刚伏魔棍等练得风生水起,有模有样的相互切磋着,渐渐有点小能耐,震慑了校外来学校闲逛的社会小青年。
快毕业的时候,王大新的各门功课除语文外考试成绩一塌糊涂。
母亲叹了口气,没有责罚,只是担心他这么小的年纪没高中上,干嘛去好?
八五年的夏季,有些炎热,知了在树上发出死不休的叫声。农村的夏收已接近尾声,母亲作出了王大新人生第一次重大转折的决定,说:
“现在年纪太小,干不了多少农活。还是去复习读书吧,万一能考上个学校,米饭白了,有个国家旱涝保收的包分配工作也是挺不错的。”
王大新从此走上了复读之路,在数学老师青睐鼓励下,把数学攻了上去,以几近满分一举夺魁,考进了有粮票领用的市级学校,一度成为今后几届复读生的榜样。
第一次跨出县域到百里之外的地区市就读,也就是从那时开始,王大新从小爱好的书法技能也大大发挥出作用来了。
颜真卿的帖本,别的同学写得珠圆玉润,王大新还写得大气磅礴,隐隐之中有将相气息扑面而来。
半学期后王大新成为了身兼多职的学校学生会干部,校报上,板报上,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十七八岁的青葱岁月,伴随着身边围绕过来的男男女女,王大新在市区的东湖,鉴湖,柯岩,兰亭,八字桥,秋瑾故居,三味草屋等处游历,印下了爽朗的笑声,无限憧憬的美好。
想到这里,王大新深深叹了口气:
“真不知道后面的二十多,三十多,四十多岁怎么蹚过来的。”
“回头看看毕业工作以来的三十年,有哪些还能勾起自己的回忆呢?”
王大新不由得过滤起来。
二十多岁的时候,似乎就谈了个恋爱,结了个婚,快三十的时候生了个娃。
三十岁后,随着国有事业企业公改私大潮,下岗大军拿着可怜的一点遣散费,涌上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,王大新也同样被推着走了。
随后几年从打工到打工,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,职位虽然不断高升,升到不能再升了,毕竟是在小地方,薪酬还是不高,一年到头手上剩不下上千的钱。
王大新第一次感觉打工到头了,凭着一股子勇气,手中还有寥寥可数的几个生意上合作伙伴,拿着几千元积蓄,走上了创业的道路。
跌跌撞撞间,王大新从三十岁迈过了四十岁,又到了四十五岁,从一开始感觉良好,到道路越来越难走。
各种各样的骗子来了,忽悠大新合作,忽悠大新去投资,各种各样的骗局,王大新不知不觉间被骗了不少。
贷款越来越多了,房贷车贷企业经营贷,付出的利息和还款,越来越压得王大新透不过气来。
原先稍有优势的产品,业务越来越小,毛利也越来越薄,王大新又一次陷入了困境,无奈地只能顺势走着,由不得自己。
四十五岁以后的日子,王大新基本上是东做做,西做做,想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出来,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
王大新在想,自己这前半生磕磕绊绊的,莫非正应证了孟夫子那段:
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?”
这几年经济一年不如一年,失业率爆发性增长,企业产值和效益进一步下滑。
一方面是很多人找不到工作,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用人,两头都拉不拢,仿佛南辕北撤的现实版故事。
王大新黯然一笑,暗暗道:
“企业的生与死,与我王大新个人命运又有何异?都是有其自然规律,有兴有衰,也有其天命的。”
“人力不可违的时候,就不要过多的去勉强,顺其自然就好了。”
隐隐约约间,王大新好像通透了人情世故,看明白了这个表象光鲜亮丽的现实世界,觉得好像自己不属于在某一地某一时刻的固定人物,只是暂时一时半会儿呼吸在此地、此时、此刻罢了。
随着最近天空灰蒙蒙越来越浓,蓝天白云日子越来越稀少,王大新眼前又出现了白茫茫的一片,看不见任何东西,突然间他失去了知觉。